
把长江看作一条长鞭,它抽在广袤的江汉平原上,溅起一片星罗棋布的湖河,再侧身绕过雾蒙蒙的大别山,湖北的格局就这样定下来了。
黄州城是我的家乡,坐落在鄂东大别山脚下。它作为黄冈市府所在,下辖着大半个大别山区,地理上却属于江汉平原。这山与原的交界地带,总带着一股与生俱来的清冷气息。
说起过年,我本该回忆一下黄州的冬天,但过往的冬天如何,只剩下一些记忆碎片了。人的记忆就是这样,并不像树苗生长一样缓慢而有序地开枝散叶,而是像夜里的雪,细碎而绵密地铺在脑海中,一不小心就拼凑出了生活的全貌,又一不小心消融得只剩些许水渍。
下雪是真正冬天到来的信号,在此之前只能称之为“天冷”,至于这“冷”是归属于秋还是冬,没有人能解释得清楚。对于孩童时期的我来说,更愿意将初雪作为过年的序曲。毕竟过年需要操办的事项与我无关,我可以早早地留心观察着家里的一切。
我家并不临街,离正宗的柏油马路还有一小段距离。那是夹杂着碎砖和石块的土路,春雨淅沥的时节,路面铺了一层黏滞的泥水,只要经过就会在裤腿后甩出几点泥印。进入夏天则又是另一番光景,太阳烤得地上开裂,碎砖块像地下埋藏的种子,经过一个春天的洗礼终于破土而出。直到冬夜的雪,从北方吹到黄州只剩下薄薄一层,轻轻地像蚕丝被一样盖住整个城市。
黄州的年关里多是夜雪,一觉醒来,窗外微妙的光亮变化让人察觉夜里落了雪。凹凸的土路也只有雪后才显出一些素雅,像一个朴素的老太太只舍得在年关里穿几天漂亮衣服。
要想欣赏到雪景,在黄州城其实是不太容易的,家门口的土路大概凌晨五点多就有了行人,车辙与脚印很轻易就带走了积雪。
我很坚定地认为我是世界上唯一留心这条土路上雪景的人,毕竟大人总是计较过年能吃些什么。
其实大人们也没错,年间最要紧的还是不同于平日的吃食。只是家里过年的饭菜其实极其乏味,母亲总是不愿意用外来的食材填充家里的饭桌,而本地的高级食材也刚刚凑够一桌年饭,因而每年的年饭菜总是相同的。
鄂东有一种家禽叫番鸭,外形与口感都介于鹅鸭之间,拿来清炖一锅鸭汤,就成了压轴的硬菜。香甜的汤水总会被母亲在口头上赋予许多额外的营养,仿佛喝上一口,整个冬天都不会冷了。
最鲜美且贵重的河鲜是青鱼,肉质紧实,纹理像页岩花纹一般。在父母丝毫不愿告诉我家里经济状况的岁月里,青鱼成了我“窥斑见豹”的最佳途径。倘若父亲悄悄地弄上几条已经腌制好的青鱼,又没有配上青鱼丸子,那必然是收成不佳了。有些较为阔绰的年岁里,父亲会让奶奶去寻上十几条上好的青鱼回来,亲自动手来拆解。
观赏鱼货的制备是我最喜欢的年间项目,鱼背刮成细茸汆成鱼丸,鱼腩滑一锅新鲜的汤,鱼骨剁开用油炸,鱼头用盐渍了炖上两个水萝卜。而忙活完一个白天,我能收获两副新鲜的鱼杂,摘几棵蒜苗,点几滴酱油,炒得黑乎乎的。
鱼丸浮在腾着雾气的鱼腩汤里,另有若干盆摆在一旁。全家人都贪嘴,在年前尝一口年后才能吃的年货。我依然清楚地记得我是喜欢看窗外的,每每吃上一碗鱼杂拌饭我都会望一眼窗外,冬日漆黑的夜里,风割着玻璃刺耳地响,屋里淡黄的光弥漫着,像乌黑茶盘上泡开的一壶热茶,倔强地牵着那一缕热气。
土路自然会被翻修,菜谱也终究还是要与时俱进。我出门念书的七年光阴,它们都偷偷改换了模样。之后再次站在家门口的柏油路上,我会觉得脚下埋着我的记忆,这些漂亮的新事物置换了我的过去。
“你肯定还是要回来的……”我母亲向来是这么告诉我的。
“我肯定是不会回去的……”我也向来是这么回应她的。
倒不是我与家乡有什么格格不入的理由,只是回乡了便会寻找,旅途上便会回忆。在近处找寻不到的,只能拉远距离去回想。
贪图这羁旅带来的思念,于我的人生而言,显得格外浪漫。
编辑:陈慧芳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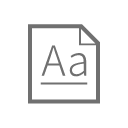 字体:+ -
字体:+ -
